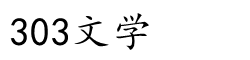最后几户灾民住到了新搭起来的草棚子里。
粥棚也搬到了这些屋室的对面。
这三日,从早到晚,施粥整整三次,比农人常用的饔飧还多出来一餐。
灾民脸上的冰雪色,渐渐在一日三顿的粥的雾气里化了,变得红润了些。
反而是萧锦的脸上的红润剥了下来,出现了菜色。
他昨日便向他的父王上表,洋洋洒洒,写了千字有余,令人快马加鞭递到了王府。
大意是“……前有雪灾,后有乱民,淮阳王府恐染是非。今虽千余人妥善安置,然,适逢年节,王府、国、县,更当勉之,切不可懈怠。”
淮阳王早就听说了萧锦立下毒誓,与民同甘共苦的事迹,读到此处,更是有了吾儿长成,可堪托付的欣慰。
而王妃在欣慰之余,听淮阳王读到了灾民挨饿受冻的惨状,心酸不已。
想到自己的独子也在一道喝淡薄的粥水,宿漏风的草庐,不啖肉味,夜不能归,足有了三日,就要落下泪来。
她用手绢拭了眼角:“阿锦,他可是金玉做的人儿啊。”
淮阳王仍看着信笺,拊掌笑叹:“有匪君子,金玉之表,赤子之心!”
王妃早暗暗存下了心,这夜的岁除家宴,无论如何,要把儿子接回王府。
但见淮阳王大喜过望,担心他突然发了磋磨儿子的心。
尤其是听见了“有匪君子”几个字,联想到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那同样磨在了母亲的心尖尖上啊!
王妃痛心疾首地顿地,引来淮阳王侧目。
“妾是想着盘鼓舞呢。”她面上浮起了笑,提议让府上女乐编了新曲,踏鼓而歌。
曲名也一拍脑袋想出来了,一支叫作《大雪歌》,一支就叫《济世行》。
“妾立刻就教她们几个抓紧练去,留待除夕夜宴,为吾儿压惊。”
最后几个字,她轻轻咬了咬唇。
萧珵心思都在那表上,只听见了“大雪”、“济世”二词,满心欣慰,就点了头。
王妃长长舒出了一口气。
只是,这口气还没舒完,却见夫君的笑容淡了,脸沉下去。
王妃引颈看去,淮阳王目光所及处,是儿子写在表上的最后几句:
“……莫若以豚肉,庆祝年节,此为灾民期愿。”
一份表上,独独这几个字,像是虎头蛇尾,龙飞凤舞,粗辨不清。
送表来的常贵低眉垂目,候在一边,等着淮阳王开金口,说出一个“准”字。
济世之行不再济世了。
不过儿子毕竟还是儿子。
哪怕淮阳王再不乐意,在护犊的王妃跟前,也不得不噤了声。
王妃拿绢帕拭了一刻钟的眼角,哭诉自己的儿子,分明是饿得连字都写不动了。
帕子上的泪痕看不出一星半点,淮阳王苦劝的唾液倒是飞上去不少。
岁除之夕,谁愿意睡书阁里的冷榻呢?
翌日除夕,不到食时,三十头宰杀好的肥猪就运到了翠微山下。
这日奔忙的,不再是王府家仆与吏卒了,热雾也不止从施粥的棚子下升腾而起。
妇人一马当先,比拼起厨艺。男子撇下耒耜,挥起了厨刀。
这比萧锦之前过的任何一个除夕都要热闹啊!
歌舞雅乐,比起一片叮叮咚咚的切剁声,少了力道。
觥筹交错,比起咕噜咕噜冒着泡的汤汁,缺了浓香。
等几口铜锅里边,肉香接了碧霄,无人能忍得了了。
雪地的篝火,映在天上,青天白日有了繁星。
千百的民众,喝汤吃肉,乐府民谣得了佳韵。
而他,萧锦,坐在这一片热腾腾的最中央。
鼻子都酸楚了。
闻着香,听着响。
偏偏一箸下去,总有更快的手,从那深不见底的汤锅里,搛去屈指可数的肉块。
周遭都是饿狼扑食似的人。
肉还没有煮透,就不见了影踪,三十头猪,六千斤,到他嘴里的,只有寡淡的,像猪的洗澡水似的汤了。
零星的猪毛浮在汤上,连带着飘落的碎雪,与周围人高声说话,与吸溜汤汁的唾沫星子。
他一点儿也喝不下去。
哪怕是他的小厮常贵,从虎口夺下了拳头大的肘子块,放在了几乎已经两日粒米未进的世子碗里。
半生的猪肉,腥臊味直钻鼻孔,冲着天灵盖而去。
他意兴寥寥,刚把碗放下,想了想,又端起来,递给了一旁的人。
究竟是谁接了过去,他没看清。
只觉得在扑面而来的人与猪的热气中,那半块肘子被卸成了八块,到了无数人的嘴里。
精壮的男子,泼辣的女子,羽翼下的幼子,犄角里的老人。
他最终从扑鼻的膻臭气,酸腐气,泥腥气中,挣脱了出来,站在了粥棚子下,立在一口已经见了底,连汤汁都被哄抢一空的铜锅跟前。
眼前茫茫的,依旧是八月的潮水。
千百的浪头,起伏着,涌动着。谈笑声,打闹声,贺岁声,争执声,忧叹声,碎碎的,飞雪一样,打在他的脸上。
林榆席地而坐,作了其中的一处浪尖。
伏在他旁边一个个小小的浪,是一群郡国学的学生。
他笑着开口问:“进食之礼?”
“左淆右胾!”一个还未束发的男孩抢答,“我方才就是这样,一手一个碗,左边的碗盛了汤羹,右边的碗,阿父为我盛了一块大大的猪腿肉!”
这话引来一阵惊叹。
贺季挨着林榆坐,朗朗笑道:“看来果真是,仓廪实才知礼节啊。”
他指了指自己跟前的空碗,“没有两个碗的人,只能连肉带汤地吃了。”
一个始龀之年的孩子却认认真真地对他说:“但是,贺夫子可以毋流歠1啊”。
贺季脸上的笑瞬息无踪。
他看了一眼人群中正在一道发笑的林鸢,轻轻咳了一声,争辩,那是因为他的陶碗缺了个口子,“就同你嘴里边掉了把门的牙一样,漏了!”
孩子们却似乎受了鼓舞,要在授礼的林夫子跟前表现一番,声音赛高:
“还有,毋吒食!”
“还有,毋啮骨!”
贺季面红耳赤:“啃骨头的,明明是陈家的那条狗!”
人群里却又传出一个童声:“那,曲礼中还说,毋——毋投与狗骨!”
还没等贺季说,并不是自己将骨头扔给了狗,林榆就接过了话,问道:“曲礼中有‘宦学事师,非礼不亲’,你们知道是何意?”
方才第一个抢答的孩子这次又争了先,朗声道:“做官学习,侍奉师长,都要事之以礼。”
林榆赞赏地颔首,贺季也忙不迭地点头。
“你们方才可不是待师之礼。”林榆一板一眼地教导那些孩子,“若真要说那些话,开头就不该称人为‘夫子’了,应该以兄弟相称才是,得叫兄长。”
说罢,他拍了拍贺季的肩,“你说是不是,贺弟?”
贺季受了捉弄,偏过身去,要给林榆一个暴栗。
几个孩子会了意,相视一笑,齐齐喊道:“贺兄,坐如尸,立如齐!”
林鸢笑岔了气,挨到了阿瑶的身上。
阿瑶被林鸢碰得发痒,边笑边歪着身子问:“他们说的都是什么意思?我都听糊涂了。方才还在说陈家那条狗呢,怎么又成尸了?那狗是吃了贺夫子——贺兄给的猪骨头,死了么?”
林鸢捂着肚子,“嗳哟”直叹,颤颤说:“还好还好,咱们几个算不上君子,不必坐得像受祭的人那样子端正。”
众人都笑成了一团,推推搡搡,挤得贺夫子的饭碗又在地上滚了两圈,半寸长的豁口变成了两寸。
阿瑶惊异地问:“姊姊,你读过书啊?”
林鸢的一口笑噎在了喉咙里,憋得脸红了几分。
她拉过羊羔裘的风帽遮住了脸,“只是在家认了几个字罢了。”
“难怪林夫子中意你!”
阿瑶接下来的叹慨,她隔着呼呼的风和一层风帽,听不清了。
那句话,萧珣也说过。
林鸢在椒房殿的紫宸阁中磨好了墨,见萧珣埋首在书卷中,没有别的吩咐,就蹲了蹲身,悄无声息地告退下去。
“回来。”
萧珣往砚上瞥了一眼,“这点墨,一会儿用完了,我自己磨吗?”
林鸢见墨砚边沿雕的飞龙,一半的龙鳞没入了墨池里,心说,哪怕是在缣帛泼了墨来作画,也够完成几尺的大作了吧。
但陛下开了金口,她断然不敢反驳。只能回到御案边上杵着,等着那“一点墨”少下去。
等到斜阳入户,为捧卷读书的人镀上了一层金粉,将玉制的笔山连同搁在上面的毛笔,变作了真正的连绵起伏的石山——一动不曾动过。
林鸢正百无聊赖,昏昏欲睡,听见萧珣让她往书架上寻山海经。
她往书架走去,心里思忖,这两日她理过书,没见过这里放着山海经啊。
脚步踟蹰,身后传来了一句:“第三层,从左数第八,随意取一册就好。”
还真是山海经。
不过,林鸢不解,方才听声音还是心情不悦的陛下,为何忽然童心大发,要看这种小儿的书了?
但她很快抱回了最厚的一册帛书。
“上头有不少画儿,你若是闲来无事,就看看吧。”
林鸢愣了愣,她比陛下小一些,可也早过了看图画的年岁了。
她称了诺。
绢帛的书,虽只一卷,但宽大厚实,像往胳膊上压了一匹布。
她不由思量,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错事,要遭今日这样的罚,一会儿得去问问王内侍才好。
“坐这儿看吧。”
“可,这是御案。”她看着萧珣指的位子,犹豫着说道。
萧珣冷笑了一声:“你怕这书案,但是不怕违了我的话?”
林鸢忙摇头道:“不怕。”
“嗯?”他蹙了蹙眉。
林鸢涨红了脸:“既然是陛下说的,那奴婢不怕这书案了。”
她将沉甸甸的绢帛放在了御案的一角。
只是不知道为何,空着的坐席离萧珣很近。
她想拉远些,但四角的铜鹿席镇细脚伶仃,俨然不稳当。
她暗自懊悔,自己昏了头,怎会无意将御案下的坐席排布了两个,还挨得这么近?
萧珣沉浸在书里,她可不敢发出动静,闹了他,恼了他。
犹疑的时候,她又听见了冷声:“还不快坐?站那儿,挡着我的光了。”
林鸢“刷”地挨着他坐了下去。
她坐如针毡,一动都不敢动。若伸开手,二人几乎就是肩擦着肩了。
旁边的人倒是安之若素。
殿中又沉寂了一些时候。
林鸢一连看了好几幅司幽之国的画儿,渐渐放松下来。
司幽生思士,不妻。一旁有列子天瑞中的注解:思士不妻而感。2
林鸢漫无边际地想:“思士不需娶妻,单是有了天人感应就能生子了。陛下一定羡慕极了。”
她满怀同情地转目,看向那位好龙阳而无子嗣的天子。
当然只敢瞥到他的手。
那手搁在书案上几乎没有移过半寸——看得真是如痴如醉啊。
她忍不住侧目,看到了那双手翻开着的书卷。
竟是兄长在家教过她的礼。
兄长少时提出,要教她识字念书。
林鸢不解地问为什么。
她每日很忙很忙,要喂猪,割猪草,在阿母的灶台边帮忙,还要同邻家的阿金阿银作过家家的游戏,以尘为饭,以涂为羹,以木为胾3。
林榆也说不上来一定要识字的缘由。
可是,他认识的女子,都识字,不仅识字,还知礼,会诗,通琴曲。
“你若会读书,会写字,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。”他想了想说。
林鸢并不心动。她不识字,不读书,照样有很多人喜欢她呀。
不过,很快,林榆那一句“书中有千钟之粟”,让林鸢眼睛发亮了。
尽管字识了几箩筐,林鸢几乎把架子上的所有书都翻过一遍了,都没有找到书中的粟米,反而书看得越多,越是腹饥,阿母搁在灶台上的饼子成倍地少了下去。
好在,连年的丰年,家里的猪牛多了起来,盅里的粟米,虽没有千钟,但也有了千升4。
阿父每日笑呵呵的,有了余钱余粮,买了车马,让林榆跟着一位大隐隐于市的鸿儒学诗书。
那位程姓的夫子听说在先帝朝时,曾于太学讲经,还在石渠阁同其余二十二诸儒,一道议论五经异同。
定下的版本,由天子钦定为“真五经”,为太学与郡国学代代所用。
后来他因病退隐,隐姓埋名住在五里外的荒山上。
程夫子自退隐之后,从不收弟子,也不再设坛讲学,不过一次偶遇,发觉林榆有慧根,答应了授书。
林榆激动不已,热泪盈眶。
向来不做孩童游戏的他,那日回家后,同林鸢,还有阿金阿银一起,过起了家家。
他将她们的尘饭涂羹次第摆好,说:“这是周礼。”
“周礼是什么?”林鸢以为,周礼是千钟粟一样的东西。
“就是周公定下的礼仪。”
“周公是谁?”阿银问。
林榆解释:“周公,姓姬名旦,乃周文王之子,周武王的弟弟,辅佐年幼的成王为政,始创了成康治世……”
八岁的林鸢一听便肃然起敬,生了想往。阿金阿银仰头听着林榆的话,不用说,也都出了神。
一个以鸡蛋为名的人,必然最是懂得如何治粟,如何持家了。
她知道市集上有一位养鸡卖蛋的张姓商户,人人都叫他“鸡蛋张”。
他靠着卖鸡卖蛋的小本薄利,建起了大宅,养鸡场都有一般人家的三进院落那么阔。
依律法,商人不许在屋前筑狮虎狻猊等瑞兽5。他另辟蹊径,请石匠雕了两个浑圆的蛋,以此来镇宅。
听阿父酒后戏称,鸡蛋张的本意是想雕两只鸡,只是,石匠的要价多出了百倍。遵循“重利轻‘意’”的原则,他自然舍弃了。
鸡既有一鸣惊人的含义,那么蛋,当然也可以是财源滚滚的意思。
左右两个蛋加上中间一扇窄高的黑漆拱门,成了长安西郊永平乡的一道奇景。
……
想到这儿,林鸢忍不住唇角微扬。
“你读过书啊?”
萧珣的声音到了她的耳畔。
林鸢才发觉自己的目光不知在那一卷礼上停顿了多久。
是多久呢?
应该不算很久吧。
毕竟,萧珣手里的书卷,一直停在那页。
“嗯,幼时同……”她刚想说出“兄长”两个字,转念却道,“同阿父学的,认得几个字。”
林鸢入宫前才发现家中的籍册上没有兄长的名字。她不明缘由,但深知利害,连李顺面前也从没提起过林榆。
李顺与她的兄长照过面,不过,早年的记忆早就被雨打风吹去了,零零落落的,只剩下了林鸢,和秦氏飘香了十来年的饼子。
“你看了这书许久,看来很喜欢看书啊。”
林鸢本想说,是这书中的画画得好。
萧珣却伸手,合上了她面前大荒经的帛画书,将手中的礼,推到了她眼前。
她的脸刷地红了,方才她盯着他手上的礼看了许久吗?
可他明明沉迷在书中,怎知她看了许久?
她还是腼腆地点了点头。
因为看到萧珣的嘴角弯了起来。
他是极少笑的。
林鸢忽然觉得兄长哄她读书时说过的话,是有几分道理的。
萧珣指了指其中的一段:“这些能读懂吗?”
林鸢摇头:“不能。”
“是哪几个字不认得吗?”
他问得很有耐心。
这语气莫名让林鸢想起了兄长,不由回答:“这两句,男先于女,刚柔之义也。”
萧珣诧异:“认得字呀,句读也没错。那是为何不懂?”
林鸢想起兄长原先教她读这一篇昏义的时候,十岁的她是很喜欢的。
她与阿金阿银几个玩过家家的时候,谁都想要争当新妇。
阿金的姊姊嫁给一个功曹史时,乡间小道上挤满了几个乡的人,她挤到最前面,用心数了数,嫁衣上,青绛黄红绿,整整有五个颜色,都看花眼了。
更别说,书里还提到了纳吉、纳征,几个字就让她想到了阿金家里,从屋里一直铺陈了整整一院子的漆木箱子,一双大雁,还有牛马羊豚。
只是,在读到“男先于女”这一句的时候,无论兄长怎么解释,她都坚持,“女先于男”。
因为,没有阿母,哪来的兄长啊?
哪怕是阿父,也是大母生下来的,而大母也是女子。
林榆拗不过她,笑说:“好好好,女先于男。兄长心里,阿鸢永远先于任何人。”
她如今长大了,不再胡搅蛮缠。
她缓缓思量道:“男子不一定刚,也有柔弱之处,女子不一定柔,会有刚强之时,女子也可以是君子。再说了,刚不一定胜于柔。所以,男子也并非先于女子。”
她忘了看萧珣的脸色。
待这些话说完之后,她也不敢看了。
心如擂鼓,在胸腔里咚咚地敲出闷响,她在沉寂下来的殿中,恍惚听见了……钟声。
不啊,是秋蝉的悲鸣,落叶的簌簌声。
那些声音里夹了森然的笑,像是天上而来,又像是灵魂出窍的自嘲:“你真敢说啊。”
“不敢,再不敢了。”她悻悻,喃喃自语。
身子因那笑里的寒意,结了冰,僵了。
“是我先问的。想怎么答就怎么答。”是萧珣的声音,“何况,你说的,也并非全无道理。”
林鸢确信这声音不是来自地府,也不是来自天庭,才回过了魂。
萧珣似乎并无愠色。
“刚与柔,不应以男女而分。古来要强的女子不少,娥皇女英,妇好,太姜太姒,周宣姜后,无盐之女。”
笑也传了过来,“还有,你。”
林鸢的脸,被这话,还有说话人落在耳边上的,酥酥麻麻的气息,灼得通红。
“姊姊的脸为何红了?”阿瑶的声音也落入了她的耳畔。
“风吹的。”林鸢闷声道,将兜着头套着的羊羔裘又拉得紧了些,只剩了一双眼。
翠微山还是冷,不过,雪已经停了多时,风也小了。
她看到鹅毛大的雪片,在半空一闪而过。
“呀,又下雪了么?”
等阿瑶抬头看去,却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“姊姊看花了眼吧。大概是大家口里边吹出来的热气。”
阿瑶偏着头,在呼出来的白气里,远远瞧见了玉树临风的世子。
一支羽箭在萧锦的眼前掠过。
箭镞擦过铜锅的一耳,稳稳落在了三尺口径的锅中。
细小的碰撞声几乎不可察觉。
萧锦回过神,惊出了一身汗,来不及唤吏卒,一手握紧了身上的秦王剑,一手发着颤,将那支羽箭取了出来。
鎏金的箭镞。
上面的印花,他认得。
是羽林骑的箭矢。
他向方才那支箭飞来的方向看去。
只见那些围坐着的人群之外,停了两驾陌生的马车。
灰色的帷帐,不饰纹绣,低调非常,看不出来自哪一个世家。
驾车的马却齐齐一色,都是毛色如缎。是大宛的马。
一个腰束玉带的皂衣男子微微低着头,躬身侧立,手上执着箭囊。
车帘拉开了一半。
满绣的袖口在风中轻曳,扬起的时候,能看见一支金箭搭在挽成了满月的雕弓之上。